Lovable 把“无代码”讲成了“一人独角兽”的新故事:不靠烧钱投流,只靠用户把平台当 AI 联合创始人;不追明星工程师,只找“斜率最陡”的学习型人才;不惧巨头围剿,自信真正的护城河是“你在我这里攒下的全部业务”。本文浓缩创始人 Anton Osika 的 90 分钟深度访谈:拆解增长飞轮、人才公式、定价陷阱,以及 AI 应用如何在模型狂飙年代守住长期主义的底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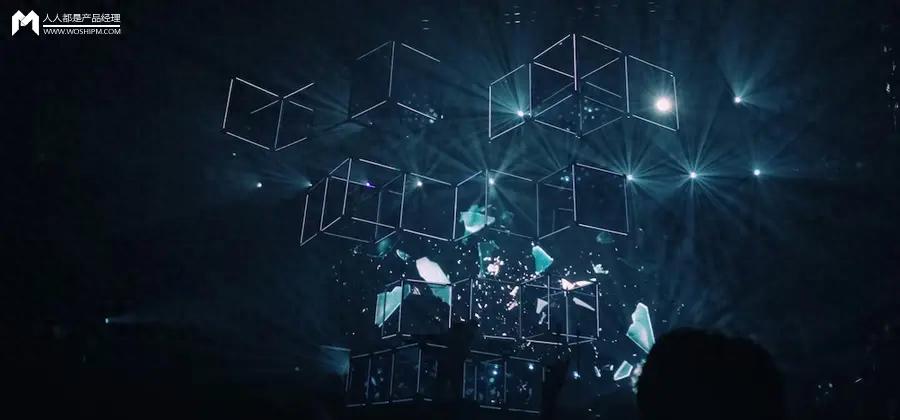
在过去的 7 个月里,Lovable 成为了硅谷和欧洲创投圈的焦点。由 Anton Osika 联合创办并担任 CEO 的 Lovable,仅凭半年多的时间就实现了从 0 到 1.2 亿美元 ARR 的跨越,并在估值 20 亿美元的融资中获得 Accel、Creandum 和 20VC 的加持。融资规模超过 2 亿美元,让这家创业公司成为 AI 应用赛道增速最快的企业之一。
在接受 20VC 对话时,Anton 系统谈到了行业现状与企业战略。从 AI 是否是一场军备赛还是人才战、如何与 Meta、OpenAI 等巨头竞争顶尖工程师,再到护城河与单位经济学的“残酷真相”。
增长、用户结构与企业市场
Lovable 在 7 个月内实现 ARR 从 0 到 1 亿美元的跨越,被认为是近年少见的增长奇迹。Anton 在对话中解释了背后的逻辑:并非依靠大规模广告或传统的渠道打法,而是通过用户需求的自然扩散和产品价值的强绑定。“我们的增长依靠用户的真实使用场景,而不是一轮轮买量。”
从用户结构来看,Lovable 的主要用户群体分为三类。第一类占比最大,约 80%,是那些以 Lovable 为工具构建复杂应用的个人或小团队。这些人把平台视作“AI 联合创始人”,从产品原型到完整应用都在平台内完成。第二类是企业内部的产品经理和团队,他们借助 Lovable 快速搭建演示和原型,用来推动公司内部的立项或产品迭代,这一类正在快速增长。第三类则是轻量用户,用 Lovable 做个人网站或小型商铺站点,占比约 10%。
Anton 指出,最核心的动力来自第一类用户——AI 原生创业者。“我们的使命就是帮助那些本可以成为创业者,但被代码和资金门槛阻挡的人。” Lovable 的出现,正好为这一群体提供了从 0 到 1 的完整工具。他们不再需要雇佣工程师或筹集启动资金,只要有想法,就能用 Lovable 实现并上线。
与此同时,第二类用户也在形成新的增长引擎。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内部,员工开始使用 Lovable 来验证产品概念。比如一位谷歌产品负责人曾明确表示:“我们再也不会只写一份产品文档,而是直接在 Lovable 上搭建一个可运行的 Demo。” 这种从内部推动创新的方式,让 Lovable 自然渗透进企业场景,而无需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销售推动。
至于第三类轻量用户,虽然在收入占比上不高,但 Anton 并未忽视。他认为这类用户能为品牌带来广泛的覆盖和心智渗透。很多人最初可能只是用 Lovable 搭建一个个人网站,但随着熟悉度增加,未来也可能转向更复杂的项目。换句话说,轻量用户是“潜在创业者”的蓄水池。
在被问到“这样的用户结构是否是最优解”时,Anton 的回答很直接:是的。Lovable 想要首先服务的,正是那些真正会用它来创业的人,因为他们会沉淀最深的价值。至于价值提取,他并不焦虑。长期来看,当用户在平台上创建和运营起完整的公司时,支付环节、增值服务和扩展功能都会自然产生新的收入流。
这种逻辑也解释了为什么 Lovable 能够在短时间内冲上 1 亿 ARR。Anton 提到,初期的付费用户往往愿意承担更高的订阅费用,因为他们把平台看作构建业务的关键基础设施。这与传统 SaaS 平台不同,后者的付费更多是为提升效率,而 Lovable 的付费则与用户的业务成败直接绑定。“当用户在 Lovable 上构建一个生意时,他们不可能轻易离开。”
对于企业市场,Lovable 的态度较为克制。Anton 强调,他们不会变成一个“传统意义上的企业销售公司”,不会投入大量资源去“请客吃饭”或“高层推动”。相反,他们关注的是让产品自然进入企业内部工作流,通过员工自发使用形成拉动,再逐步向组织扩展。他把这称为“企业敏感度”,而不是“企业销售团队”。
这种方式带来的结果是,Lovable 在企业市场的渗透速度比想象中更快。虽然目前企业用户在收入中的占比只有约 10%,但增长曲线明显陡峭。尤其在欧美大型科技公司,Lovable 已经开始被用作内部创新工具。Anton 判断,随着企业逐渐适应 AI 在数据权限和安全上的要求,这部分收入会在未来几年快速放大。
在外界看来,Lovable 的用户增长像是“野火燎原”。但 Anton 坦承,这背后依旧存在瓶颈。其中之一是如何同时满足大量涌入的企业需求与个人开发者需求。企业客户要求高安全性、权限管控和长期稳定,而个人开发者则追求速度与灵活性。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,是公司必须解决的问题。
他还提到另一个长期挑战:如何在“心智份额”与“利润优化”之间做权衡。短期来看,Lovable 会继续优先扩大用户规模,让更多人把 Lovable 当作默认的应用构建工具;而利润优化则可以推迟。Anton 甚至直言,当前更重要的是“让更多人爱上这个品牌”,而不是追逐毛利率。
这种心态也与他对 AI 行业整体的理解相关。在 Anton 看来,AI 应用的市场空间几乎无法用传统方法测算,就像当年的 Uber 一样,最初被理解为“打车软件”,但随着市场扩展,才展现出远超想象的规模。Lovable 也一样,远不止是一个“无代码建站平台”,而是一个全新的软件构建范式。
因此,对 Anton 而言,1 亿 ARR 只是开始。真正的终局,是成为 AI 原生时代的基础设施,让“一个人创办独角兽”成为可能。
人才与团队构建
在 AI 创业赛道,资本是否是决定性因素始终存在争论。Anton 的看法是:真正的军备赛不是拼资本,而是拼人才。如果目标是训练最顶尖的基础模型,算力和资金或许是关键;但对于 Lovable 这样的应用层公司而言,更重要的是能否迅速组建并留住一支卓越的团队。资本能够帮助,但“钱”并不是限制因素。
在人才争夺上,Meta 通过“签下 NFL 球员合同”式的天价薪酬吸引顶级工程师。Anton 并不认为这是 Lovable 应该效仿的路径。他指出,应用层公司的用人需求和基础模型研发公司完全不同。即便那些擅长训练大模型的专家加入 Lovable,也未必能在产品迭代中发挥最大价值。Lovable 更看重的是那些能适应组织节奏、在团队中推动文化和产品突破的人。
对他而言,“招聘的关键不在于点值,而在于斜率”。如果在与候选人的交流中,能明显感受到启发与知识增量,说明这个人可能会快速成长并适应公司,这往往比履历更加重要。Lovable 不追求简历上最耀眼的头衔,而是寻找那些能在动态环境中保持学习力和适配度的人才。
在早期阶段,Lovable 也并非一开始就追求明星级管理者,而是愿意与“不那么显眼”的人共事,随后在关键时点引入重量级人物补位。比如 Elena Verna 的加入,就帮助公司在增长和组织建设上更进一步。Anton 甚至直言,他在招聘中会关注一些“非显性指标”,例如候选人是否经历过极端创伤或展现过极端执念。他认为,伟大的品牌总是有强烈的观点,伟大的人才往往也带有某种“极端”的色彩。
在组织方式上,Lovable 仍然延续“创始人模式”的主导氛围,但同时也在建立一层“保护层”。这层保护层由前创始人背景的多面手组成,协助过滤外部干扰,保持信息的高效传导。Anton 把它形容为“混乱中的保护网”,通过快速反馈和密切协作来维持公司节奏。他自己并不计划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“有条理的管理者”,而是要确保身边有能把控组织秩序的领导者。
进入增长阶段后,Lovable 开始探索“混乱与秩序”的平衡。Anton 坦言,公司依旧在很多地方保持着初创时期的“野路子”,但在几个关键领域必须逐步增加结构化和秩序感。这种张力既是挑战,也是 Lovable 高速成长的核心特征。
护城河与商业模式的真相
在 AI 创业中,护城河和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是外界最常提出的质疑。许多评论者直言,AI 应用公司缺乏真正的防御性,用户迁移成本低,核心能力依赖模型供应商,难以在长期形成稳固的价值。Anton 并不回避这一点,他坦率指出:品牌固然重要,但防御性最终必须依赖产品本身。
在他看来,所谓防御性,最强的形态不是外界看到的融资规模或者市场声量,而是让用户在产品中沉淀越来越多的价值。当一家公司的平台能够成为“你不愿离开的地方”,那才是最强的护城河。他举例称,Lovable 的目标就是成为创业者和开发者的“AI 联合创始人”,不仅帮用户写代码,还能协助处理财务、运营、增长等环节。一旦用户把公司运营的全流程都放在这个平台上,自然不会轻易迁移。
在收入结构上,外界常批评 AI 应用公司“单位经济学糟糕”,因为大量收入最终会流向底层模型供应商,如 OpenAI 或 Anthropic。Anton 并不否认 Lovable 的早期收入中,大部分确实直接付给模型提供方,但他强调这是阶段性现象。随着用户对 Lovable 平台价值的认同感提升,订阅收入和产品增值服务会逐渐成为主要来源,而 AI 算力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成本。
他提出了一个形象的类比:AI 创业公司就像“被大炮打上天空的小鸡”。每天都会有新的公司被“发射”出来,数量庞大,轨迹各异。但能否存活,不取决于起点,而在于谁能飞得更快、持续得更久。换句话说,短期竞争靠速度,长期竞争靠平台价值和用户沉淀。
在定价策略上,Lovable 也探索过不同的方式。Anton 透露,早前公司统计过平台上所有 AI 调用的流量,结果发现仅这些调用,就已支撑起超过 1000 万美元的 ARR。但这一模式的弊端是用户需要经历复杂的模型接入流程。Lovable 的下一步目标是“让一切更简单”,并在降低底层成本的同时,逐步增加可控的毛利。换言之,初期的商业模式以“买量和跑通”为主,后期才是优化利润率的阶段。
在被问及“是否应该从第一天就考虑防御性”时,Anton 的回答是:不必。创业初期更关键的是执行速度和增长轨迹。当用户规模与市场心智占领达到一定水平,防御性自然随之而来。这种观点与许多硅谷投资人强调的“先拿下市场,再考虑护城河”逻辑高度一致。
另一个被提及的隐忧是:应用层是否真的需要追逐最先进的模型?毕竟,很多使用场景只需要稳定、廉价的模型即可完成任务。Anton 认为,当前阶段仍不适合过早做模型优化,因为每个月 AI 模型的能力都在快速更新。与其为了今天的某些场景定制,不如为“明天的能力”留出空间。Lovable 的策略是始终构建面向未来的应用,而不是过度优化当下。
这种思路也体现在 GPT-5 的应用上。Anton 认为 GPT-5 在多个维度上表现出色,尤其在解决复杂问题时优势明显,因此 Lovable 已经将其集成到平台。但同时他也承认,GPT-5 并非所有场景的最佳解,有时候甚至过于“雄心勃勃”,因此 Lovable 仍然保留了 Anthropic 等模型的接入选项,形成“多模型链路”,根据不同任务智能调用最合适的引擎。
在商业模式的长期演进中,Anton 还特别强调“心智份额”的重要性。他承认自己听取过 Revolut 创始人的建议,对方强调应尽快算清获客回报周期,优化利润结构。但他个人更倾向于“先争取用户心智,再考虑利润最大化”。在他看来,当用户大规模依赖 Lovable 构建产品和业务时,价值提取的方式会自然出现,而不是需要一开始就穷追毛利率。
这种思路与传统 SaaS 的发展路径有相似之处:早期通过低价甚至补贴快速扩张,后期逐渐依赖增值服务、企业合约与深度绑定来实现盈利。不同之处在于,AI 应用的市场空间更不可预测,Tam 的扩张几乎无法用传统行业类比。Anton 把 Lovable 的未来比作 Uber——早期被误解为“打车公司”,直到市场扩展才显现出远超最初认知的规模。他相信,Lovable 的真实市场也远不止“建站工具”,而是一个全新的软件构建范式。
对于竞争者,他并不避讳表达看法。有人质疑 Lovable、Replit 等公司在安全性上存在漏洞,他回应称,“如果把平均水平的个人开发者与 Lovable 生成的应用相比,后者的安全性反而更高。” 因为平台会自动执行多重安全审查和漏洞检查,最终才能放行产品。就像自动驾驶汽车并不完美,但相比多数疲惫或分心的司机,整体上更加安全。
当谈到防御性是否仅靠品牌时,Anton 再次回到用户价值的逻辑:最强的护城河不是别人抄不抄得了,而是用户有没有足够的理由留下来。“如果你的平台能帮他们省时、省钱,还能完成独立做不到的事,他们不会走。”
GPT-5 与应用迭代
外界普遍认为它是 OpenAI 的又一次重大升级,但 Anton 的评价则更为谨慎。他承认 GPT-5 在复杂问题解决上表现突出,但同时直言:“这不是一个性能跨越式的飞跃,更像是一种整合。”
他的分析是,OpenAI 将原本分散的多个模型收敛为一个统一的 GPT-5,这在用户体验上更清晰,也更符合产品化逻辑。但代价是:在追求“一体化”的过程中,模型在某些维度上必然会有所妥协。之前的多模型体系,能在特定任务上发挥极致优势;如今统一到单一模型,意味着在部分细分场景中不可避免地“短板化”。
Lovable 团队在决定是否接入 GPT-5 之前,做了多重评估。他们不仅测试了响应速度、准确性,还在真实用户场景中进行验证。结果显示,GPT-5 在代码调试和复杂推理等高难度任务上表现出色,但在日常轻量化需求中,反而显得“过度复杂”。因此 Lovable 的策略是:将 GPT-5 集成进产品,但并不取代其他模型,而是作为多模型链条中的一个选项。“对用户来说,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用哪一个模型,而是能否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。”
这种多模型协作的理念,也正是 Lovable 产品的一大特点。平台会自动将用户输入的信息拆分,再传递给不同模型:轻量、快速的任务交给小模型,涉及复杂逻辑时则调用 GPT-5,而在代码生成方面,Anthropic 的模型依旧是首选。这种“链式架构”既保证了效率,又避免了单一模型的局限。
在 Anton 看来,真正的挑战并不是哪一家模型更强,而是如何围绕模型构建起最优的用户体验。模型是快速演进的,但用户的工作场景和需求却相对稳定。Lovable 的价值,在于把最新的模型能力无缝融入应用构建流程中,而不是让用户去学习如何写 prompt、如何在不同模型之间切换。“我们构建的不是一个更好的模型,而是一个更好的入口。”
对于 GPT-5 的具体表现,Anton 认为它在“深度思考”上表现突出,能够解决复杂的调试问题,但这并不是 Lovable 用户的日常刚需。大多数情况下,用户需要的是快速、稳定、低成本的解决方案。因此 Lovable 必须在“前瞻性”与“实用性”之间取得平衡:既要让用户体验到前沿能力,又不能牺牲迭代速度。
他特别指出,过早地围绕某个模型进行过度优化是错误的。原因在于模型迭代速度太快,今天的优化可能在一个月后就失效。相比之下,更重要的是保持平台的灵活性,让它随时能够接入“明天的模型”。这种思路本质上是“为未来而建”,而不是为当下做微调。
当被问到“是否应该担心 OpenAI 或 Anthropic 直接进入应用层,与 Lovable 正面竞争”时,Anton 的回答依旧是强调执行力。“很多人都会提供我们今天在做的东西,但关键在于,当那一天到来时,我们能不能提供更多。” 在他看来,模型公司与应用公司的分工会越来越清晰,真正的胜负不在模型,而在于谁能提供最佳用户体验。
在这点上,他并不讳言对 OpenAI 的敬意。他认为 OpenAI 在消费者体验上的执行力优于 Anthropic,这也是为什么他更把 OpenAI 视作直接竞争对手。但与此同时,Lovable 的差异化在于定位为“AI 联合创始人”,覆盖的不仅是对话或问答,而是完整的产品构建、运营和增长链路。
在商业角度,Anton 也谈到 GPT-5 带来的定价与成本问题。由于用户对 Token 定价并不敏感,理论上应用层公司可以在 Token 使用上叠加溢价,从而实现毛利扩张。但他同时指出,这并非 Lovable 当前阶段的重点。现阶段,公司更专注于降低用户接入成本,让用户无需复杂配置就能直接使用模型。只有等平台沉淀足够的用户价值后,才会考虑通过 Token 定价或增值服务来优化利润。
在战略层面,GPT-5 也验证了 Anton 一直坚持的观点:最重要的不是今天模型的能力,而是如何利用“明天模型”的潜力去构建应用。 未来,当模型越来越具备常识推理和复杂场景处理能力时,Lovable 已经在产品层面做好了快速对接和迭代的准备。
对于行业普遍担心的“模型能力天花板”,Anton 的态度相对乐观。他认为,在语言和通用能力方面,确实会出现边际递减,但在科学研究、工程设计和生物医药等领域,AI 依然会保持指数级进步。换句话说,GPT-5 或许没有带来“科幻式飞跃”,但在一些垂直场景中,AI 的潜力远未触及极限。
在总结 Lovable 与 GPT-5 的关系时,Anton 再次回到用户体验的角度。他认为用户并不在乎底层调用的是哪一个模型,关键在于“产品能否帮我更快完成任务”。Lovable 的使命,是把复杂的模型能力抽象掉,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享受到最新的 AI 成果。
本文由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作者【江天 Tim】,微信公众号:【有新Newin】,原创/授权 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,未经许可,禁止转载。
题图来自Unsplash,基于 CC0 协议。
















